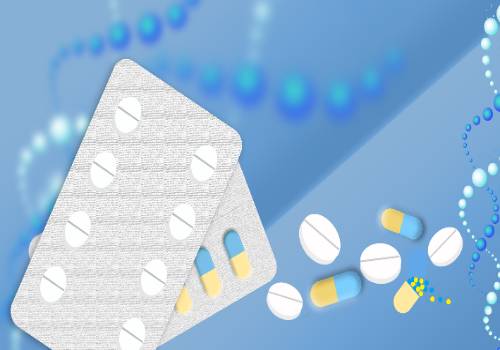(三中)
寒假很快就在爆竹声中过去了,随着寒风的渐退,新的学期又将开始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和相处,师生之间,同学之间已十分熟悉,宝乾优异的学习成绩,自然受同学们的尊重,尤其是他的语文能力也引起了语文老师注意。
语文老师是一位三十开外的男教师,姓田,名容。他在当时的语文界中略有名气,也不时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古体诗歌,及文学评论之类的文章。在批改学生作文时,他发现宝乾的作文与其他同学大不相同,尤其是十分到位地引用古典诗文的做法,不用说在他的同龄人中少有,即使是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也难以做到。有时田老师甚至怀疑眼前的文章,是否真的出于宝乾笔下。
学期开课不久,田老师决定找宝乾聊一聊。星期五下午,老师和同学开始离校了,宝乾按田老师的嘱咐,来到了语文科办公室。
办公室里,只有两三个老师还在批改作业,田老师的办公桌就在室内尽头的角落里。
“老师们好,田老师好。”宝乾站在办公室门口,有礼貌地行了一个礼。田老师十分高兴,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说了声:“请进”。
宝乾小心地来到了田老师跟前,田老师则从别处搬来了一张椅子,请宝乾坐下。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学习,对田老师,宝乾是早就认识了的,可现在却感到有点陌生,眼前这位笑眯眯的师长,为什么找自己谈话呢?正当宝乾犹疑之际,田老师说话了:
“你猜,我为什么找你来?”
宝乾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不知道。”
“不用紧张,只不过是聊聊天,谈谈学习而已。”
听田老师这么说,宝乾更觉得奇怪了,“学习”,不就是听课,做作业吗?有什么好谈的呀?于是十分小心地说:“是不是我在上课或作业上有什么问题了?”语调中带有一点担心和疑虑。
田老师明显感到眼前这个学生,十分文静,善于思考,他正在努力试探着将要发生什么事。于是直接说:
“你平时爱读些什么书呢?”
“我没有什么特别喜爱读的书,但我以前看得比较多的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文选》……”一说到读什么书,宝乾就滔滔不绝说了一大串,田老师也越听越觉得奇怪了,这么小的年纪,怎么能读懂这样多的子、史、经书呢?田老师急忙打断了宝乾的说话:
“你家里都有这些书吗?”
“有呀。”
“能告诉我,你双亲的大名吗?”田老师心里估计宝乾一定是生长于书香世家。
宝乾把自己家里的情况,及在村中跟随陈慧学习的事,简单地告诉了田老师。
田老师明白了,眼前这个学生的确与众不同,他是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柢啊。田老师显得有点兴奋了,于是试探地问:
“郑庄公所以能称霸一方,原因是什么呢?”
这个突然而来的话题,让宝乾愣了一下,但他很快就明白,田老师是试探自己是真的读了一些书,还是在卖弄一些书名,夸夸其谈,于是想了一想,小心地答道:
“照我看来,主要是两个字:"忍’和"孝’。其弟共叔段为非作歹,肆意夺权,庄公其时刚登位,根基未稳;且共叔段的不仁不义尚未为国人认识。于是庄公一再忍让,既企望其弟悬崖勒马,不要一错再错;亦藉此让国人看清真相,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。事情平息后,虽深知母亲姜氏实为主谋,但庄公却在取得民心的同时,坚持孝道,注重母子之情。在当时以仁、孝为先的社会里,庄公的表现越发取得国民的拥戴,所以史家评论说:"孝子不匮,永赐尔类’。”
田老师听后,大喜,他想不到眼前这个学生,对这段历史能作出这样扼要、得体的评说,对传统文化竟有如此深的思考。田老师信服了,他为自己收了一位可堪造就的弟子,感到由衷的高兴。这时,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已回家去了,室内只有田老师和宝乾两人。窗外的阳光只剩下一点余辉,原先约好放学后到操场锻炼的几个同学,不时往窗内窥望。时间已不早了,田老师笑着说:“外边这些同学在等你呢,不要让他们等得太久了。”于是对宝乾鼓励了一番,并表示以后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,可以随时和他交流。宝乾向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,然后把椅子搬回原来的地方,便缓缓地走出了办公室。田老师目送着这位有礼貌,举止得体的学生,宽慰地笑了。
从此,他们师生两人,也就成为了好朋友。
一天,田老师告诉宝乾,学校准备搞一次演讲比赛,希望他能够参加这次比赛。对田老师这个要求,宝乾没有一点思想准备,什么“演讲”啦、“比赛”啦他从来也没有见识过,更不用说尝试过了。对此,他显得有点为难,问田老师:
“怎样比赛呢?讲些什么呀?”
“内容没有硬性规定的,讲一件自己感触最深的事就可以了。讲完后再由老师评出谁的事写得好,谁的语言运用得好。”
听老师这么说,宝乾觉得这只不过是写一篇文章,然后再讲述文章的内容而已,何况老师现在是主动建议自己参加,这是不好拒绝的,也就答应下来了。
对这次演讲比赛,宝乾一点也不敢怠慢,他写了又改,改了又写。在班里找来了几个要好的同学,对着他们讲了一次又一次。同学不禁惊奇地发现,宝乾竟有如此的魅力,他的每次试讲,都把他们吸引住了。
这次演讲比赛是全校性的比赛,不分年龄,不分年级。宝乾演讲的文章是《我的母亲》。他把自己对生母的思念,对袁妈十多年来倾注到自己身上的、像母亲般的爱,和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,都浓缩到这短短不足十分钟的演讲中;那出自肺腑的真情,驱动着一声声纯朴的语言,感染着听众,传达给了每个评委。演讲结束后,会场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。田老师高兴极了,当宝乾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,他忙迎上去,拍着宝乾的肩膀,连说:“真想不到!真想不到!”
在中国的大地上,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,便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,不但军阀混战,水旱虫灾频仍,更遭到列强的欺凌。这些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,关乎民族命运的大事,过去在乡村时却是不知不闻。自从到了省城读书后,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宝乾不但从同学口里,从老师的讲授中,知道了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事;更从报纸的报道中,知道了因天灾人祸,列强入侵,所造成平民百姓忍饥挨饿,四处飘零的痛苦生活。这些凄怆的情景不时闪现在宝乾脑海中。
下午放学后,他又来到田老师的办公室,他真希望田老师能帮他解开日间所见所闻、所带来的忧虑。
“前几天,高年级的同学搞了一次为河南一个小县城的募捐活动,这些钱财真的能送到灾民手里吗?”
田老师还以为宝乾这次也和往常那样,谈些学习、诗文等问题,对宝乾的这个发问却是毫无准备。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是。
“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?”田老师只能这样反问一句。
“我昨天在街上看到一则标语,说"专员可耻,侵吞公款’。如果这是事实,那募捐的钱财,岂不是被这些人私占去吗”。
田老师听后,长叹了一声:“这些事,我们平民百姓哪里管得了?贪赃枉法的事,何时不存在?你想想,有些人整天不干活,可是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,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?不就是靠搜括民脂民膏,贪污枉法得来的吗?”
田老师想了一想后,又说:“你知道前两个月武汉大水吗?”
“听说死了不少人,有些还逃荒到我们这里呢。”
“这次大水,可有人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呀。那些主管救灾物资的官员,竟擅自把筑防水坝的麻袋提价。本来按规定,麻袋中装豆与沙的比例是七比三,他们却私自改为三比七,从中贪去了大量的豆子,在市场中出售。”
田老师停了一会,又说:“这不知是天灾,还是人祸了。”
“那该怎么办?”
“不说你这样小的年纪了,就算其他人,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的,太腐败了。”
说到这里,田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,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看,你还是不要想那么多了,安心读好书,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。”
宝乾本来也不是想研究这些社会现象,只不过这些天来,不断听到一些传言,心里有点不舒畅,总想找人求证一下而已。但听了田老师这一番话后,心情却是更难平静了。灯红酒绿下烂醉如泥的官员,夹杂着泥砂、尸体的滔滔洪水,失去了亲人、衣衫不整的灾民,一幕一幕在脑中出现。这天晚上,宝乾辗转难眠,一个个字,一句句诗,在他心中涌现:
“卖儿悲,卖儿喜。卖儿终身作奴婢!奴婢虽苦辛,眼前不即死!”
“劫残人贱奈儿何,昔日朱门见荆杞!孤儿襁负走天涯,天涯处处乱兵起!乱兵虽暴未足伤,有时尚得归乡里。最伤苛政猛于虎,吸人脂膏到骨髄。纷纷酷吏急索租,买儿曷足官租抵?孤儿别母啼呱呱:饥寒但恐无人买!”
“嗟哉天下有心人,爱群爱群竟如此!”
学校的教学程序并没有因社会的动荡、学生们日益繁多的社会活动而受到干扰,宝乾也和同学一起,除了在假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,还是像平常那样上课,完成作业。他总是以优异的成绩,令同学们羡慕地,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获得了学校颁发的奖金。对宝乾一次又一次获得奖学金,八姑和袁嫂乐在心中,自不用说,就连一向不管家事的叔和也觉得脸上有光,偶然也惦念起孩子来了。
在饭后的闲聊中,叔和小声地问姑姑:
“宝乾在省城住得好吗?”
八姑也捉摸不着这个一直很少与自己言谈的侄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其实对在省城读书的宝乾,她已全交给了袁嫂,有袁嫂在,她就一万个放心了的。对宝乾的情况,她只是每个月在袁嫂回来取生活费时随便问几句,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。但因为每逢济生回乡时,都对宝乾赞不绝口,夸八姑把宝乾送到省城读书是有眼光,八姑也因此感到有点满足,更是完全放下了这门心事,专致于念经诵佛了。现在叔和这一句话,倒是勾起了她对宝乾的思念,其实,不是为了宝乾,她也早就想到省城去看看的。于是她说:
“想儿子,就到省城去看看呀。”
叔和要的正是这句话,不过他却是一个从未出过门的男人,要他自己到省城去,他是绝没有这个胆量的。现在见到姑姑有这意思,便说:
“我们一起去,好吗?”
“到省城,可没有人整天陪你聊天,也不能整天睡大觉呀。”
“就一两天,还可以的。”
“到省城,要找地方住呢,得准备一下。”
一个星期过去了,又是一个星期,终于等来了济生的来信。在信中,济生表示,若不嫌地方浅窄,可以在家中接待他们住上几天。
出门可不是一件小事,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,那串佛珠是八姑必不可少的。叔和可就麻烦了点,他自己深知,虽则是几天的时间,但住的是叔公的地方,凡事都要循规蹈矩;最令他觉得难过的是,在济生家中没有闲人可以整天陪着自己聊天,又不能自己到茶楼里消磨时间。然而,对儿子的思念,又让他把一切都忍受下来了。
平时,济生是很少在家的,整天忙于粤港澳的生意,来来往往指导和检查各部门的工作。他有一子,一女。儿子叫仲晖,是香港银座旅业的总经理;长女叫金悌,是香港一间慈善机构的干事。论辈份,他们是八姑的堂弟与堂妹,但由于与叔和年龄相差不大,宝乾也就直接以“姑姑”称呼她了。自从济生到省城居住后,他们就很少见面了。金悌他们知道这几天两姑侄来暂住,也就和父亲一起回省城与他们相聚了。
济生的家并不豪华,就在城内豪贤路的民居当中,可却是够宽敞的,是一座三层的小洋楼。平时主人家很少在这里居住,只有两个佣人负责日常管理,偶然一些来往的亲戚朋友,也往往习惯地在这里借宿一两天。
久别的堂叔侄相聚,自然是问长问短,回忆儿时的趣事,但宝乾那文静、清秀的模样却特别引起金悌的兴趣。她有意与宝乾攀谈起来:
“读几年级了?”
“现在是初三。”
“哦,快毕业啦。这么多年也不来我这里玩?”
“真不好意思,学校活动多,功课也忙,放假又忙着回乡,所以忘记来看望你们了。”
“学校有些什么活动呢?”
宝乾就把最近参加救济灾民,声讨贪污腐败的官员,出墙报,搞展览,到街头宣传等活动,说了一遍。
“你不怕被警察抓起来?”
“我们年纪小,警察是不管我们的。不过前几天有两个高三的同学,被带到警察局了,但很快就放了回来。”
“哦,是这样。以后你可要小心呀,不要自己乱来。”
夜幕慢慢降临,用过晚饭后,他们一行人坐上了济生的小汽车,欣赏广州的夜景。街道上色彩斑斓的霓虹灯,闪烁着耀目的宣传广告;油头粉脸、花枝招展的男女,还有那些不时遇到的衣衫褴褛的行乞者,都在他们车窗前闪现。叔和看着车外的夜景,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,不断询问:那是什么商店,这是什么茶楼……。八姑却紧皱着双眉,不断转动着手里的佛珠,嘴里念念有辞。济生看到八姑这付模样,知道这个一向礼佛,慈悲为怀的侄女,对眼前的一切有点不习惯了。
X 关闭